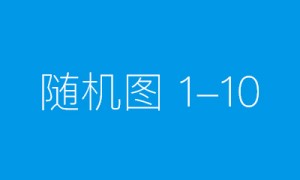华东师大外语学院陈俊松教授发表在国际期刊Partial Answer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A&HCI)上的论文“Jewish Settlement in Shanghai during WWII in Fiction and Other Media of Cultural Memory”高度评价了贝拉的《魔咒钢琴》,他称《魔咒钢琴》是第一部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出自中文作家笔下故事背景设在上海的犹太人小说。
有人说贝拉作品体现的强烈人道主义内核是引起关注的原因;也有人说翻译家的译本比中文原著好(莫言也同样遭此质疑)。由于涉及犹太文化题材抑或从未见过第二个中文作家那么专注中犹跨民族跨文化跨宗教的文学探索,那些犹太顶级精英如迈克麦德沃,巴瑞莱文森、罗伯特库恩,罗纳德哈伍德,葛浩文……都赋予了贝拉作品更广阔的世界。

美联社新闻:贝拉小说成奥斯卡编剧哈伍德最后的绝唱
贝拉开始受到瞩目的分界线是三年前她返回北美定居。我发现像她这样有信仰的作家,既深爱自己故乡与祖国,又具如此勇敢无畏灵魂、敢于直面上海特殊时期下的人生救赎,非常难得。
最近看了她新著上半部,太震撼了,八个字概括:大可期待、皆有可能。
当各种纷争战火正在摧毁人类的文明,这位生活在西方的上海女子试图以文字的银针缝合撕裂的世界版图,以文学呼唤和平,以故乡展现人道。
犹太学者埃利·维瑟尔曾说:”美的对立面不是丑,是冷漠。”而贝拉正用她灼热的笔尖融化历史与时代的冰原,让《魔咒钢琴》的旋律穿透历史尘埃,《幸存者之歌》的回眸凝聚犹太民族的灵魂;《海上金殿》的光辉点燃童年的异乡;《911生死婚礼》的烛光照亮文明裂隙——这位手持文学火炬的和平祭司,在三大洲文明交汇处编织着超越民族的精神史诗。
在黄浦江雾霭笼罩的清晨,贝拉以《魔咒钢琴》拉开被岁月封存的记忆琥珀。二战时期犹太难民与上海市民共同谱写的生存交响曲,在她笔下化作88枚黑白琴键的宇宙隐喻——当犹太钢琴家亚当的肖邦夜曲与上海女孩李梅的梁祝在石库门屋檐下缠绕,文学的炼金术将苦难超越种族的精神之都。这部被美国汉学家葛浩文曾预言“世界影响力超越所有他翻译的当代小说”的犹太人在上海的人道主义史诗,其扉页镌刻的犹太谚语:”拯救一个人,就是拯救整个世界”。
葛浩文的预言是正确的,之后本世纪英国最伟大的剧作家罗纳德哈伍德将其改成了《钢琴师2》 ,重现了犹太人在二战时期的逃亡生涯。
如果说《幸存者之歌》是犹太青年的东方漂泊史,那么《911生死婚礼》则是贝拉向文明伤口注入的文学疫苗。当双子塔的尘埃尚未落定,这位勇敢的书写者已深入时空断层,让世贸中心废墟中迸发的婚礼誓言成为全球文明的抗体。此书的美国翻译家Ann Huss在英译本序言中写道,”恐怖主义的死亡赋格与人类之爱的安魂曲在纸页间永恒角力。”
文学炼金术的普世价值呈现在贝拉的叙事中,语言是穿越文学迷雾的隧道。她拒绝廉价的伤痕展览,而是以存在主义显微镜观察人性切片:上海弄堂老裁缝为犹太孤儿改制的旗袍内衬里,藏着《妥拉》经文;911现场飞舞的婚纱碎片上,映照着《圣经》诗篇;这种糅合了卡夫卡式荒诞与杜甫式悲悯的叙事语法,使她的作品成为跨越文明断层的地质罗盘。
在法兰克福书展的穹顶下,当不同肤色的读者为同一段文字落泪,当希伯来语与汉语译本在柏林墙遗址旁散发书香。贝拉用文学证明了歌德的古老预言:”世界文学的时代又将来临。”这位坚持用汉语写作的和平使者,正以文字搭建通天塔的脚手架——不是钢筋混凝土的傲慢之塔,而是用眼泪、音符与婚礼玫瑰构筑的精神方舟。
在瘟疫与战火交织的午夜,我们或许该重读贝拉写在英语版《911生死婚礼》卷首的启示:”被击落的飞机已化作一架架钢琴,世贸废墟上都已长出了玫瑰,半空中的云彩是天堂与人间的婚礼殿堂。”这位手握文学圣杯来自上海黄浦江畔的女作家,用世纪的悲欢离合熬煮成一剂解药:让音乐战胜枪炮,以亲吻消弭仇恨,教玫瑰开满弹坑——这便是贝拉作品最朴素的救赎公式。
当黎明前的黑暗最浓稠时,总有人率先点燃火种。不用多久,在纽约、东京、伦敦、巴黎与耶路撒冷的书店橱窗里,那些烫金封面的贝拉小说,正像永不熄灭的和平长明灯,等待为迷途的文明导航。(罗文)